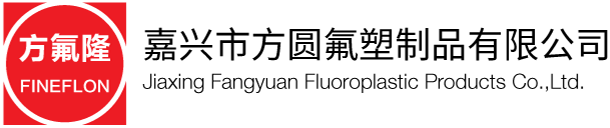有必要在向 Arvin 提供建議時進行審查,其中舉證責任在于 Arvin 被指控的罪行的每個要素。被控人可以通過舉證責任和舉證標準在Actus Reus和Mens Rea兩點上證明,以證明被告的行為和意圖。Viscont Sankey LC [ 1 ]規(guī)定的刑事案件的一般和基本規(guī)則 是,控方必須證明犯罪的所有要素,排除 合理懷疑。Woolmington v Dpp [ 2 ] 并且在被證明有罪之前,Arvin 有一個無罪推定,如 ECHR 第 6 條第 2 款所述,因為需要舉證責任和高標準來證明斷言是正確的。
為了證明當事人在刑事審判中的責任,被告必須讓陪審團相信他們是無罪的,或者檢方必須讓陪審團相信他們有罪。然而,這里要解決的問題是,該法規(guī)是否撤銷了對犯罪任何方面的法律舉證責任,是否可以在任何方面將舉證責任放在被告身上,或者法律責任是否應(yīng)僅由控方承擔。
正如在給定的法規(guī)中,議會的意圖是控制誰在沒有合法借口的情況下故意行為構(gòu)成犯罪,如果被告表明他們正在歸還書籍和部分,那么他們對所有人都有有效的辯護,包括法律學生證明的證據(jù)。

正如普通法原則“主張者必須證明”。證明誰在沒有合法辯解的情況下故意行為犯罪的問題通常是在控方身上,但是在辯方和控方之間,證據(jù)和法律責任可以分開,正如在 Hill v Baxter [ 3 ] 中Devlin J 給出的概念 一樣較重和較輕的版本 [ 4 ] 。Thayer [ 5 ] 描述了他的特殊責任,他有任何特定提議的風險,如果他不提出這個提議,當所有的事情都已經(jīng)說了又做了,他就會輸?shù)舭讣?/span>
一般規(guī)則是,承擔法律責任的人也承擔舉證責任 [ 6 ] 。對這個問題給出的法規(guī)的分析可以參照這個版本 [ 7 ] 。羅伯茨 [ 8 ] 指出,證據(jù)責任根本不是嚴格的舉證責任,而只是舉證責任(L v Dpp [ 9 ] ),但事實上,它仍然是法官一個人的責任 。負有法律舉證責任的一方也對該問題承擔舉證責任,并有義務(wù)提供足夠的證據(jù)來提出實體法規(guī)則所確定的問題 [ 10 ] . 如果根本沒有證據(jù),或者如果證據(jù)不能像哈爾伯里勛爵在 Wakelin v London SWR [ 11 ]案中所說的那樣使事實發(fā)現(xiàn)者滿意,那么責任方就會敗訴 。
正如在 Hill v Baxter J Devlin 案中所說,被告有舉證責任 [ 12 ] 提出足夠的證據(jù)來提出辯護問題,但控方承擔了反駁辯護的法律責任。控方的法律責任是在整個審判過程中排除合理懷疑地證明被告被指控的犯罪的每一個要素,但控方的證據(jù)責任是就被告所指控的每個犯罪要素提供相關(guān)且可接納的證據(jù)。被指控并有責任提供足夠的證據(jù)來提出實體法規(guī)則所確定的問題 [ 13 ] 。
在 Hunt [ 14 ]的案例中, 賓厄姆勛爵提到了格里菲斯勛爵的聲明,如果法規(guī)不明確,法院應(yīng)該考慮其他因素來確定議會的意圖,例如該法案所針對的惡作劇和影響負擔的實際考慮證據(jù),特別是當事方在履行責任時會遇到的難易程度。有可能在法規(guī)的措辭上,檢方似乎有責任證明阿爾文故意不歸還書籍。然而,Dowrkin [ 15 ] 認為,人們有絕對的權(quán)利不被他們無辜的罪行定罪。
賓厄姆勛爵在 AG 參考文獻 [ 16 ] 中 指出,舉證責任不是舉證責任 [ 17 ] 。舉證責任取決于案件中的證據(jù),即有關(guān)問題適合事實法庭審議的問題。如果一個問題被恰當?shù)靥岢觯敲礄z察官必須在排除合理懷疑的情況下證明該免責理由對被告無益。法律責任決定了他在指導陪審團如何達成裁決時所說的話 [ 18 ] 。然而在民進黨訴謝爾德雷克案 [ 19 ] Clarke LJ 表示“繼續(xù)使用它來減輕負擔以識別引發(fā)問題的證據(jù)是明智的”。在蘭伯特[ 20 ] 和約翰斯頓 [ 21 ]的后續(xù)案件中 ,上議院根據(jù) 1998 年人權(quán)法第 3(1) 條和歐洲人權(quán)法院第 6 條[ 22 ]考慮了公平、相稱和合理性的檢驗標準 。
尼科爾斯勛爵還解釋說,為了維持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平衡,不應(yīng)將僵化和僵化的標準強加于立法機構(gòu)試圖解決困難和瞬息萬變的問題 [ 23 ] 。在 Dpp v Sheldrake [ 24 ] 中,上議院審查了一個涉及辯方的案件中的舉證責任狀況,以將舉證責任放在被告身上,以證明被告在相關(guān)問題上沒有可能性。Salabiaku v France [ 25 ]案中的斯特拉斯堡判例 并不意味著檢察官的舉證責任是絕對的。在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取得合理的平衡很重要。
在這里,Arvin 可以表明他相信書籍沒有過期,并且他沒有故意行事,因為他忘記了,并且在途中被逮捕,并且在第 (4) 款中的辯護不是一本受歡迎的書可以免除其作為檢方舉證責任的舉證責任,可免除著名案件和基于法定例外的抗辯。通過考慮與歐洲人權(quán)法院第 6 條第 2 款有關(guān)的反向舉證責任和無罪推定 [ 26 ] 的舉證責任問題,導致被告有罪的責任始終由檢方承擔的命題和任何懷疑都應(yīng)該有利于被告 [ 27 ] 。在 R vlambert, R v Ali, R v Jordon [ 28 ]案 中,在反向舉證責任的背景下,法規(guī)中的證明可以解釋為強加舉證責任,Steyn 勛爵表示,立法干預無罪推定需要正當化和不得過于自由,但必須遵守相稱性原則 [29 ] 。
總結(jié)證明標準仍然是向法官和陪審團展示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或概率平衡的證明。強加于控方的舉證標準是為了免除合理懷疑的舉證責任,并出于政策原因而采用的證明標準是公平的,而不是錯誤地將無辜者定罪。然而,正如丹寧勛爵在米勒訴養(yǎng)老金部長案[ 30 ] 中所說的那樣,這種證明仍然是一個高度的可能性 。
盡管如此,它仍然存在問題,因為什么構(gòu)成了無可置疑的合理懷疑,如相當確定 [ 31 ] 或滿意 [ 32 ] 或合理確定 [ 33 ] 或合理滿意,所以你能被戈達德勛爵確定 [ 34 ] 但是在斯蒂芬斯的情況下 [ 35 ] 上訴法院對以前的案件進行了區(qū)分,并確定陪審團應(yīng)該被告知他們必須滿足,這樣他們才能確定有罪。在 Carr-Briant Lord Humphreys [ 36 ] 的情況下 指出法律責任在被告人身上,在證明可能性時免除責任,除非證明相反,陪審團應(yīng)該被指示由他們來決定所需的舉證責任低于所需的證明責任。起訴在證明案件排除合理懷疑的情況下,可以通過使陪審團滿意的可能性的證據(jù)解除。根據(jù)給定的法規(guī),被告被要求證明他所知道的某些事情。把負擔放在他身上是一種相稱的反應(yīng),保持了公共利益和個人權(quán)利之間的平衡。
由于羅伯茨和祖克曼[ 37 ] 指出,精神病例外的實際意義有限,因為精神錯亂意味著強制拘留在醫(yī)院,因此無罪是無罪的,因此阿文不可能就精神錯亂辯護進行辯論 。
正如 Mundy 認為的 [ 38 ], 人們不應(yīng)該逃避 Lambert 的想法,即議會可以合法地將法律舉證責任強加給被告。在蘭伯特關(guān)于無罪推定的情況下,立法有一個選擇。首先,除非滿足概率平衡,否則將法律舉證責任強加給被告;其次,僅將舉證責任強加給被告。正如本案中的短語“被告人要證明的辯護”,并認為如果控方提出了被告人有罪的證據(jù),辯方必須舉出一些不知道該實質(zhì)性質(zhì)的證據(jù)。在 L v DPP [ 39 ] 法院考慮了 1988 年刑事司法法第 139(4) 條,并將法律責任放在被告身上,以證明他有充分的理由或合法權(quán)力作為對第 139(1 [ 40 ] 條 )指控的辯護 。
根據(jù) 1980 年 s101 地方法院法[ 41 ] 的 規(guī)定,法定默示例外的問題可以在爭議中確立 ,如果被告依賴任何例外、規(guī)定、豁免、借口或資格作為辯護,他承擔舉證責任例外。上議院認為,這頒布了一項普通法原則,即該法規(guī)可以隱含地將舉證責任從起訴轉(zhuǎn)移到辯護。
如果被證明,舉證的法律責任在于控方說服陪審團排除合理懷疑,被告確實了解實質(zhì)內(nèi)容的性質(zhì)。就像約翰斯頓[ 42 ]的情況一樣, 如果被告表明他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標志的使用而不是他在給定法案中的有效辯護。 深圳律師事務(wù)所
| 南園路律師解析不良品格證據(jù)對陪 | 福田律師談莎莉克拉克 |
| 福田律師解析陪審團是一群人聚集 | 福田律師談上訴法院陪審團聽證醉 |